步入21世纪,夏文化探索进入积淀深究的新阶段。二里头、新砦、王城岗等遗址的新发现刺激了有关夏文化问题的讨论,其中以早期夏文化探讨最为热烈。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新媒体急速发展,夏文化探索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本文以夏文化探索的关键问题为纲,立足《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所收录18位专家学者的访谈内容,简要介绍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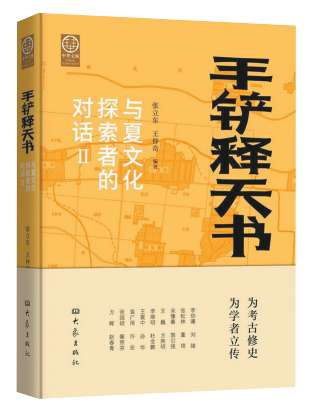
何为夏文化
夏文化概念兼具考古学与历史学色彩。徐旭生先生在《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中提出“夏文化一词很可能指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1977年“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先生总结性地提出“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
目前,学界探索夏文化时大多以夏鼐先生所提定义为基础。不过仍有不少学者对此做过探讨。王巍先生、王震中先生的访谈中涉及到夏文化定义问题。
王巍先生认为“夏鼐先生的定义是比较准确的”,他说道“夏文化是指夏代以夏族为核心的以及臣属于它的一些小的邦国构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这实际上是在夏鼐先生的基础上,对夏文化的时空范围、族属范围和文化内涵进行了扩充和说明。王震中先生认为夏是“复合制国家”。他认为夏文化应为“夏王朝时期夏后氏(夏王族)的文化”,“把夏文化定义为夏的王邦及王畿所在地的文化,会更合适一点”,“实际的可行性要高一些”。这实际上是对夏文化的空间、族属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
“夏文化”定义是夏文化探索的概念前提。夏文化定义的探讨隐含着不同学者对夏王朝时空范围、族属、文化内涵的判断;对考古学文化、族群与王朝转化对应的理论思考。目前,各家夏文化定义主体相近,细处有异。随着夏文化探索的深入,这一问题将无法回避。恰当的回答该问题不仅有助于夏文化研究,更有助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进步。
夏文化之首及夏代积年
夏文化之首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夏文化本体的指认。目前,关于夏文化之首的探讨主要有两类基本态度:一是早期夏文化要在二里头文化之外寻找(探索对象包括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后岗二期文化等);二是早期夏文化要在二里头文化中寻找(探索对象包括“新砦类”遗存、或排除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等)。这两类观点在时间、空间上均互有重合、矛盾之处。但其症结多在“夏代积年”问题上。
李伯谦先生对夏文化有系统性看法,他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与新砦期遗存是早期夏文化探索的主要对象。张松林先生在郑州地区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认为“所谓的新寨期其实就是嵩山北麓地区二里头一期文化遗存,只有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才能与夏代早期遗存相当”。张国硕先生认为夏王朝应自“启”始,新砦期遗存就是早期夏文化。王巍先生认为夏代前期遗址发掘尚不充分因而对当时社会面貌不是很了解。这也是赞同早期夏文化要到二里头文化之外去寻找的态度。方燕明先生曾主持瓦店遗址发掘,并认为该遗址可能与“阳翟”或“钧台”有关。赵春青先生认为新砦一期城址为“夏启之居”,新砦遗址第二期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阶段的遗存。方辉先生认为“河南龙山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进入夏,二里头一期后是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王震中先生亦认为夏文化的年代应从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开始。
袁广阔先生虽然认为二里头文化不是夏文化的全部,但他受王国维、沈长云先生的影响,认为“夏代早期主要活动在河济地区”。他提出“后岗二期文化为早期夏文化”,“新砦期文化不是早期夏文化”。
刘绪先生敏锐地意识到文献记载的夏积年可能过长。他推算夏代与二里头文化年代跨度大致吻合,认为“夏代起始之年可能没有那么早”。孙华先生也表示“偏向刘绪老师的看法”。这一观点否定了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的记载,提出此观点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文献记载夏世系有所缺漏的可能。
董琦、李维明先生承续邹衡先生的学术体系探索夏文化,认定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郭引强先生亦信从此说。董琦先生认为有学者将“王城岗大城与‘禹都阳城’时期、新砦遗址与‘后羿代夏’时期、二里头遗址与‘少康中兴’时期相对应,是混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表现”。李维明考订新密黄寨遗址出土的牛肩胛骨上有“夏”字,在某种程度上为该说提供了文字证据。
要之,虽然各家学者将考古遗存与历史事件对应说法不一,但“早期夏文化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的观点似乎得到更多学者的支持。近些年早期夏文化探索的主要对象也集中在王湾三期文化及“新砦期”遗存上。
夏文化之尾
夏文化之尾的讨论多表现为夏商及夏商文化分界的争论、新旧“西亳说”与“郑亳说”的争论、“偃师商城界标说”的争论。
李伯谦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亳’没有问题”,也同意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实现了“商灭夏”的政权更迭,但具体发生在哪一段,先生自述“因为没有做过完整研究,也不敢说的太绝对。”王巍先生与杜金鹏先生坚持“偃师商城界标说”。杜金鹏先生在偃师商城的考古实践中放弃了原先夏商文化分界于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的观点,转而认为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一期1段的年代约当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是夏商文化的分界界标。作为“三期四期分界说”首倡者的孙华先生,其观点亦稍有变动,他认为“夏商更替的社会变动发生在二里头遗址第三期以后,第四期中的某个时段”。
刘绪先生曾撰写多篇文章对“偃师商城界标说”进行质疑。他虽倾向“郑亳说”,但未曾论证郑州商城一定是亳。他认为受发掘工作限制,“南亳”“北亳”之说的讨论空间尚存。
董琦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成汤亳都所在,是夏商文化主要界标点。宋豫秦先生在豫东、鲁西地区的考古工作及对夷夏商三者关系的讨论,可视作他为“郑亳说”提供的佐证。郭引强先生曾与蔡运章先生合作《商都西亳略论》,认为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也是盘庚所迁之殷。他在访谈中表示当时研究“思路并不十分清晰”。李维明先生则始终坚持“郑亳说”,他在郑州二里冈出土的牛肋骨刻辞上补识出“乇”字,“为郑亳说补充了商代文字证据”。张国硕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王太康以后到夏桀的夏代中晚期文化”,并用“主辅都制”解释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的关系。赵春青先生同样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晚期的遗存。
方辉先生考察“南关外期”遗存,认为其是夷商联盟到达郑州之后在二里头三、四期之际短时间之内形成的遗存。袁广阔先生则着眼于二里头遗址大型建筑的废弃与偃师、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中外来文化因素的出现,认为“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王震中先生也认为夏商文化分界在第三、四期之间。
综上,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二里头四期某段划限;二是二里头文化全为夏文化;三是二里头三四期之间划限。目前来看,第一种观点影响更为广泛。各家说法最多也仅在一期之差,或可说已经迫近通过考古学来考察政治历史变动的极限。夏商更迭之争的另一表现则为汤都亳地望之争。至于亳都所在,各家仍有争议,不过“郑亳说”更为强势。
夏文化探索的态度与展望
李伯谦先生坚信有夏,并认为“夏代年代学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王巍先生着重强调考古学家的作用,并非只有发现文字才能断定是不是夏。孙华先生认为夏代发现文字的可能性很小,但并不意味着识别夏文化非要有文字证据。
刘绪先生认为夏文化的上下限仍是主要问题,对待夏文化应积极探寻。同时,刘先生以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为例,说明未来夏文化探索将走上多学科结合的道路。方辉先生认为“夏王朝、夏文化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同样提倡应该引入科技考古,尤其是与人骨相关的生物考古方法探索夏文化。
董琦先生提醒道“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夏文化仍在探索阶段”。方燕明先生的态度较为审慎,他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从考古学文化转换为夏文化、夏王朝、夏族的路径”。因此他重视手头材料的重要性。赵春青先生认为寻找公共墓地是目前新砦遗址发掘急需开展的工作。杜金鹏先生指出“盘桓在信古、疑古、有夏、无夏以及二里头是夏非夏等问题的纠结中……对推进夏文化研究并无多大益处”,他认为夏文化探索即将迎来新的上升期。
李维明先生积极考释二里冈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中的早期文字,并取得一定成果。袁广阔先生亦在积极探寻夏代文字线索,他将某些晚商甲骨文、金文象形字字形与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器物的器形进行对比,进而推定该字的创造、使用年代。张国硕先生重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期待文字材料的发现。方辉先生相信夏代有文字,但因文字载体不易保存,故而发现文字“可遇不可求”。
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并不肯定是夏。他认为目前有关夏文化问题各位学者提出的各种说法皆是“推论和假说”。许先生将自证性文字作为判定夏的最主要依据。孙华先生认为若没有充分证据,则不应轻易否定夏代的存在,作为考古学家有责任通过物质文化资料去探索夏代,无论其能否实证。他认为根据考古材料研究与夏时期相当的历史,可以冠以“夏”字,亦可以不用“夏”字。
此外,秦照芬女士则对当前形势下台湾夏史及夏文化研究前景感到忧虑。
总之,几乎所有学者都将“更广泛地开展田野工作”作为夏文化探索的展望。这无疑将会为夏文化探索积累更多材料,推进夏文化探索进程。大部分学者密切关注夏代文字问题。这是探索夏文化道路上不可忽视的议题。部分学者已经在积极寻找夏代文字线索。夏代年代学研究仍然是关键,如何处理14C测年数据、文献记载及人骨材料所示寿限之间的矛盾有待考量。还有不少学者提醒我们需要关注与夏王朝所处时空范围相近的考古学文化。此外,就考古学科发展来看,科技考古及多学科合作是探索夏文化的必由之路。部分学者在面对夏文化课题时表现出纠结,甚至略显矛盾的状态值得注意。如此复杂的心态或可折射出夏文化探索课题的“时代性”。目前学界对夏文化本体的研究略显不足,结合诸位学者对夏文化探索的展望来看,未来直击夏文化本体的研究成果将会陆续出现。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
编著:张立东 王仲奇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